[导读]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,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,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“自由诚可贵,面子价更高,若为性命故,二者皆可抛”。活着成为最高价值,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?

《我的前半生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,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,对于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,源于认罪服法的交代材料的“灰皮本”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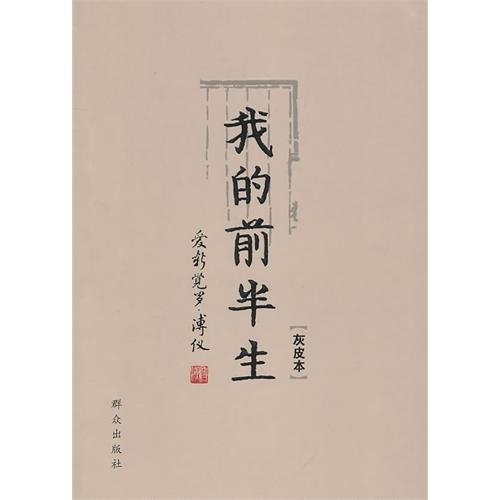
末代皇帝溥仪是个世界级的奇人,所以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外国人将其事迹拍成电影,而且多国多地参与,拍成之后获得了1988年度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奖。其所依据的除了庄士敦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之外,就是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。《我的前半生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以来,已经发行了两百万册,是部非常畅销的书。
然而这部书在市场上发行的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。一是群众出版社2006年8月第23次印刷本。这个版本基本上是1964年的初印本,只是前面加上了溥杰写于1987年的《序》,以及凌云写的《〈我的前半生〉是怎样问世的》,后来“全本”出世后,它又称为“定本”;二是2007年1月,群众出版社又出版了“全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,这个本子比“定本”增加了十六万字;三是2011年1月还是群众出版社出版的“灰皮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。这三个本子可能会使一般读者眼花缭乱,十分困惑,都叫《我的前半生》,作者都署名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,自然会使人们产生哪本是真、哪本是假的疑问。
可以笼统地说,这三个本子都是真的,作者都是爱新觉罗·溥仪,但细讲其来源,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“灰皮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可以说是这本书的“祖本”,印得最早,早在1960年1月便已印刷出版。因为是“政法系统内部发行”,当时内部发行的许多仅供参考的书,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,为了好辨认,大多用灰色纸做封皮(也有用浅黄色的),大家习惯称之为“灰皮本”,这个本子当时印量不多,据说只有八千本。
这个本子源于认罪服法的交代材料。1950年代初,“忠诚老实”运动之后,出现了一个写自传的小高潮,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员都要写自传。1954年我上初中时的作文题就有“我的自传”。这在社会上,在监狱里,那就更为严格。改造犯人时强调“深挖犯罪根源”,这必然涉及个人的经历,述说出来也就是“自传”。溥仪的弟弟溥杰在1987年为《我的前半生》写的序中说,溥仪和溥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认罪材料,他们都“努力总结自己的前半生,各自写出了一些东西”,管理所“对溥仪的特殊经历和他那几年以来思想变化颇为重视”,就让溥杰帮助溥仪详写他的经历与思想变化。于是由溥仪口述,溥杰笔录,完成了这本四十五万字的认罪类型的“自传”。当时溥杰感到,它不太像书。后来,这个认罪材料,油印出版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领导同志都看了,而且都给予了肯定。公安部因势利导,要求群众出版社组织出版,这便有了“灰皮本”。
“灰皮本”不能完全算正式出版物,不仅因为其中还有瑕疵,被领导同志指出,而且有些地方还是犯忌的,这都需要进一步修订。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陈毅副总理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,争取正式出版,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。于是,群众出版社派本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帮助溥仪“修订”。李觉得原本问题很多,很难以简单的删增来解决。经出版社领导与原作者溥仪同意,他在此本基础上、并通过调查考证(出版社专门派人替他搜辑资料与核对史实),“另起炉灶”,写了一个五十余万字的本子,也就是后来说的“全本”。这个本子经过各个方面领导和专家审看,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、何干之都提出重要的修订意见,作家老舍替他们把文字关,在通力合作下完成了这个被视为最佳的“定本”,应该说这是个比较完整的本子。但也应看到当时正值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”时期,忌讳颇多。比如张勋复辟时,有个邮传部侍郎名叫“陈毅”的,都被删去。溥仪本人正在与后来的妻子李淑贤恋爱过程中,怕书中所涉及的他与第四位“妻子”李玉琴的感情纠葛(李文达曾采访李玉琴,有第一手材料)影响了他的新生活,也被删去。当时还从政治角度考虑,李文达完全隐身于幕后,作者只署名溥仪。此本在大陆和香港公开出版,轰动一时,销量以十万计。
经历了“文革”,群众出版社并没有废弃李文达的那部未经删削的“全本”。当上个世纪那些历史条件都消失的时候,于2007年“全本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出版。这个本子除了恢复了因历史条件删去的内容外,也恢复了许多文学描写,当时有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,把这些芟夷殆尽。因此“全本”不仅内容远较“定本”丰富,读起来也更有兴味一些。
前面说到“灰皮本”距今已经有五十年了,有了“定本”“全本”之后,它还有什么意义呢?为什么五十年后再让它重新问世呢?从版本学角度来看,三个本子的差别,就显示出它们各有所长,用市场经济的语言说就是“各有各的卖点”。
“灰皮本”的卖点在于它是现存成书的最早的本子,是个原汁原味的本子,不像李文达操觚的“定本”“全本”。那两个本子,虽然也出于溥仪口述,但执笔者李文达是公安部属的工作人员,他的意见肯定有决定性的影响;而“灰皮本”则不然,虽然执笔者也非溥仪自己,但溥杰是他弟弟,肯定不敢违拗哥哥(旗人尤其重礼),何况这个哥哥还当过皇帝。因此这个文本,从史学角度来看价值更大。
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,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,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“自由诚可贵,面子价更高,若为性命故,二者皆可抛”。活着成为最高价值,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?因而,作为“认罪材料”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“犯人求生心态”。这与铁窗之外、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。因此,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,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、取悦于社会主流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。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“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”,“把自己说的太坏”,他说的也就是这种“犯人心态”。
例如如何认识他在宫中时教他英语的英国师傅庄士敦。我们从庄士敦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和后来溥仪对庄士敦为人和事迹叙述中可见他对这位“洋师傅”是有好感的。可是这一节的题目就是“庄士敦和我崇拜帝国主义思想”,文中把他说成是“英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”、“祖国人民的敌人”。其实,当年溥仪作为青年人(只十六七岁),厌倦清宫腐朽没落、死气沉沉的生活,厌恶宫中的礼制,平时连到大街上走一走、看一看的自由都没有,他向往摆脱这种专制的桎梏,逃离皇宫,到欧洲去旅行、游学,怎么就叫“崇拜帝国主义”呢?这与那个时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国人必是该国“间谍”“特务”的主流舆论有关。另外,关于胡适见溥仪的过程,“灰皮本”介绍起因、过程与结果都与实际不符,其中有谎言,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。
关于起因,溥仪说自己只是新装了电话“好奇”,“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”。实际上这件事在当年胡适日记(参见《胡适日记》1922年5月、6月)和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有记录,溥仪的“回忆”是靠不住的。
庄士敦与《新青年》许多同仁都很熟,他们都是北京“文友会”的会员。庄士敦在二十年代初还担任了一年的会长,次年就是胡适接任,两人很熟。在1922年5月17日,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前,庄士敦就对胡适说过,溥仪喜欢诗,曾读胡适的《尝试集》,胡适听了就送给庄士敦一部《胡适文存》,也托庄士敦转送给溥仪一部,可见溥仪与胡适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。溥仪通过庄士敦和胡适的书早就对胡适有一定的了解了。5月17日他给胡适打电话,要求第二天胡适到皇宫看他,胡适因为有事,没有答应,约定阴历五月初二(阳历5月30日)进宫。胡适届时前往,在养心殿中与溥仪对谈二十分钟,胡适告辞(因为他下午还有约会)。胡适在5月30“日记”中写道,溥仪除了谈到当时的新文学问题,表示他赞成白话外,又谈到“我们做错了许多事,到这个地位,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,我心里不安”。表示他个人想谋独立生活,清理皇室财产,但受到老辈人的坚决反对,因为溥仪一独立,他们就没有依靠了。溥仪谈到这些,分明有求得外界理解与支持的意思。这些决不是单纯“好奇”、“只是想看一看”胡适。
胡适走后不久,溥仪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:“久欲见先生,今日相见,深为欣快。上次先生给吾之大作《胡适文存》,良深钦佩。”信中还述说了清皇室数十年来为政不知变通,招致外侮,“且太后用海军费修颐和园,只图一己之私欲,对于人民置若罔闻。独不思一草一木,从何而出,正吾民之脂膏耳。彼以此等倒行逆施,万恶愚妇,原不足论。独惜我堂堂中华大国,为一二守旧人所坏也。德宗本欲变法,太后不惟不允,反出帝于瀛台,百般虐待,此非外人所能知也。后来中国国民知此守旧之朝廷,绝不能持,故有革命之思想。余甚赞成彼等之国家主义,不惜身命而改革此旧腐政治”(《文献·故宫(微博)琐载》)。如果说溥仪与胡适见面时,溥仪或许为了敷衍、说点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话,事后就没有必要再写这一封与他退位皇帝身份不相称的信了吧!因此,溥仪在“灰皮本”中关于庄士敦及与胡适会见的叙述和评论不仅不符合事实,而且其中是否有违心之言也值得研究者考虑。从“灰皮本”所看到的溥仪尽量趋附社会主流意见的做法,是不是与他在东京审判中作伪证(否认自己用黄绢给南次郎的亲笔信)有一脉相承之处?
《我的前半生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,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,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,“灰皮本”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。

